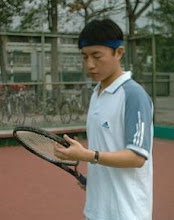.JPG)
.JPG)
「搭輪船沿恆河南下,可欣賞孟加拉農家生活樣貌,沿岸黃麻與稻田隨風搖曳成金色波浪,有時可見海豚跳躍,更能體驗河之國的發達船運。」因旅遊書的一句簡短建議,我捨棄七小時的車程,改搭一天一夜的輪船。
航行孟加拉主要河道的客貨輪船,僅有六間雙人艙房,雨季之外的季節,一床難求。艙房的有錢人,手持攝影機紀錄沿岸河景,多數當地乘客伴著雞鴨、米糧、家電用品橫臥在貨艙地上。為了禮遇外國人,船長讓我在艙房的長椅睡一晚,隔天中午過了大城巴里薩爾(Barisal)才有床位可休息。
船開抵庫爾納(Khulna)已是深夜十點,這艘大船由孟加拉首都達卡沿著恆河下游錯綜複雜的帕多瑪河(Padma River)南下,在河流與小島之間穿梭,漂流大河三十小時,誤點五小時後,鳴著刺耳嘶聲,緩緩停靠終點碼頭。
除了我,來自英國的大學生馬克是船上唯一外國人,我們相約同行,一起找住宿,揹著大背包隨人群上岸,穿過夾道等候親友的群眾,搭上三輪車,前往旅遊書介紹的廉價旅館。
市街一片靜寂,僅有少數小攤亮著燈泡,柔黃光暈投射髒亂路面、破陋屋舍,三輪車伕仰躺狹窄座椅安睡,這座孟加拉第三大城靜如鄉野,即便在深夜,也令旅人感到心安舒坦。
車伕擅自拉車到別家旅館,央求我們更改住宿地點,馬克大動肝火,辱罵車伕,猛踹車輪。車伕才駛到指定的旅館,收車資時,聳聳肩,一臉無辜。我和馬克住進五樓二間相鄰的單人房,每晚只需二百塔卡(約台幣一百元),我假裝沒看見房內蒙了灰塵的桌椅被單,但蚊子嗡嗡繞旋,即使夥計掛妥蚊帳、燃點蚊香,蚊子仍循蚊帳破洞在我腳指狠狠叮咬,我在風扇嘎嘎聲與馬克拍打蚊子的咒罵聲中,沉沉睡去。
清早,清真寺宣禮塔優緩莊嚴的晨禮召喚聲歇止,我到頂樓陽台鳥瞰晨光市景。薄霧散去,灰紅相間的水泥與磚材建築雜亂交錯,對面頂樓打赤膊圍著兜裙的男子如廁後,提水桶沖馬桶,刷牙漱洗,一會兒,出現在一樓街邊向我微笑揮手。街頭人潮漸現,婦女劈柴打掃,烏鴉飛聚塔樓,紡織廠機器轟鳴作響,閃亮晨曦中,庶民真切的生活,皆顯溫暖美好。
我先到旅行社報名隔日前往紅樹林三角洲孫德爾本斯(Sundarbans)的行程,接著搭船轉車,前往三十公里外的巴凱爾哈德清真寺古城(Historic Mosque City of Bagerhat)。當我下公車,一名瘦小男孩牽著三輪車對我招手微笑,另名成人車伕旋即以車頭撞開男孩的車,模樣凶狠,令我打消搭三輪車參訪七個清真寺的念頭。
比起達卡漫天開價、油腔滑調的三輪車伕,庫爾納的車伕多數是文盲,也不欺生,車伕逐漸聚攏,個個連英語數字都說不清,見我堅持不搭車,失望而散。
唯獨男孩踩著三輪車沿路尾隨,他的雙腿剛好鉤到踏板,痀褸的身形,難以跟車伕聯結,我從未見過童工車伕,不禁動了惻隱與好奇心。男孩強調他十三歲,雙腳有力,能操簡單英語和阿拉伯語,當我止步,就拉著我的衣角,哀求我上車。
男孩戴著穆斯林白帽,手腳傷疤累累,膚色黧黑,我們佇在烈日下比手畫腳,當他聽不懂時,只好吐舌微笑。男孩的笑,卸下我的心防,我沒問車資就上車。男孩以跳踩的方式,奮力踏車,屁股遠離椅墊,趿著大拖鞋的腳板,一如小孩開大車,極不協調。被一名只有我一半體重的孩童載著,坐立難安也難堪,仿若所有路人以指責的眼光盯我,二百公尺的距離,有如二公里一樣長。
巴凱爾哈德清真寺古城,是庫爾納唯一可看的景點,雖名列世界文化遺產之林,卻鮮少外國觀光客造訪,即使在著名的薩特庫巴清真寺(Shait Gumbad Mosque)也無提供導覽解說,我只能參考書上簡介,領略寺內七十七個圓形拱頂之美。
男孩在禮拜堂虔誠膜拜,表情肅穆,他的白帽繡著駱駝,三輪車貼有駱駝、月亮、圓頂清真寺貼紙,禮拜跪毯掛於車桿,虔心順服伊斯蘭教教義與真主阿拉。原本哼著歌謠的展覽館的女收票員,竟以阿拉伯語Shukran問候男孩,並敘述男孩曾遭人口販子拐騙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擔任賽駱駝騎士的悲慘遭遇。
男孩名叫羅尼(Rone)七歲那年,為助家計,遭人口販子以介紹到城市工廠當童工為由,淪落異鄉五年,負責照顧與駕馭比賽的駱駝,十一歲身軀漸長,加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斡旋,才隨數十名孩童被遣返孟加拉。回到家鄉,人事已非,無法融入原生社會,成為邊緣人。
羅尼脫下白繡帽,翻開帽子內裏印有阿拉伯文及英文標籤,證明這是杜拜某賽駱駝俱樂部的帽子。我看著羅尼鎮定的表情,懷疑這是博取同情的謊言,期待能獲得更多的車資與導覽費。
我在清真寺花園廣場遇到一群中學生與當地旅遊團,他們衣著光鮮,團團圍住我,熱情與我攀談,以照相手機猛拍,我甚至抱著嬰孩與數十人合影。在此享受偶像明星才有的尊榮,合照、微笑、握手,費了一小時才脫身。
我對孟加人圍觀的動作頗感厭煩,我早明白旅行僅是觀看與被觀看,可是一句簡單的「抱歉、不」卻說不出口,頓覺自己是當地居民,他們才是觀光客,而羅尼始終在旁咧嘴笑著。
我和羅尼協議互換角色,由我駕車載他到下一處寺群,這才體會踩車的艱辛,當我搖晃著車頭,小腿使勁踩踏,羅尼坐在後座開懷哼歌,一台路過的公車車窗探出許多頭,有人鼓掌加油,我揮動帽子回應他們的熱情。
遊畢七個寺群,我們坐在湖畔歇息,西斜的陽光投射藍色水面,小而美的清真寺面湖而踞,圓頂倒影映在浩如瀚海的湖面,微風輕揚,芭蕉葉沙沙作響,婦女孩童在此沐浴、戲水,浪花四濺、笑聲滿盈,小雞咯咯叫。
在這安詳舒緩的風景裡,羅尼談起中東生活的甘苦。每次照料的駱駝出賽前,會向阿拉許願,祈求贏得好名次,也保佑自己能在黃沙滾滾的畜牲奔跑驚叫聲中,拉緊粗繩,安抵終點。想家時,就哼唱母親教他的孟加拉歌謠。刺眼的陽光映射著羅尼的臉,他哼著輕快歌謠,瞇成一線的雙眼,淚光閃閃。
眼前這名命運多舛的男孩,只想單純賺點錢或結識朋友,期待早日開一家販售穆斯林宗教文物的小舖。我對於自己先前的猜忌感到愧疚,畢竟累積多年的旅行經驗提醒自己,詐騙的伎倆,日漸翻新,越貧窮的國度,越會利用人性的弱點,交織出看似完美的騙術。有了與達卡三輪車伕,討價還價的痛苦經驗,在背包客罕至的孟加拉鄉村,我只能提醒自己理性小心,別再誤觸人性陷阱。
羅尼的家位於公車站牌旁,是一間以鐵皮、草棚、大芭蕉葉拼湊而成的低矮平房,屋後是大片翠綠金黃的黃麻田,他的母親在路旁擺設茶水攤,販售奶茶與檳榔,獨立撫養五名子女。羅尼的母親急忙拿溼毛巾幫他擦汗,羅尼露出靦腆且幸福的笑容。我坐在攤前悠閒喫奶茶等公車,靜觀這家人的日常生活,羅尼母子目送我上車,一句「願阿拉保佑你!」溫暖我心,萍水相逢的熱情,僅能以多一倍的車資,表達內心的感激。
在紅樹林三角洲沒水電的小島,婦女結伴捧著水罐打水,農民餵雞鋤田、劈柴生火。每日晨昏漫步鄉間小路,隨羊群的步伐前進,熱情的居民不斷邀我入內參觀,他們樂天知命,不乞求金錢、文具、零食。日落後小島漆黑靜默,漫天飛舞的螢火蟲停棲髮梢,蛙鳴相伴入眠,小島的生活讓人感受到與萬物共處的和諧。 我為了一窺世界最大紅樹林的神秘樣貌,搭了半天馬達駁船到三角洲,卻未見孟加拉虎、印度巨蟒、鹹水鱷魚等珍稀動物。還飽受蚊蟲叮咬,過著點油燈、以河水沐浴的原始生活。隨行的船伕說,我是三個月內唯一的觀光客,他每月收入才五十美元,不懂觀光客為何花大筆金錢到此旅遊,達卡動物園就有許多孟加拉虎可看。
回到庫爾納後,我決定再搭一趟輪船,才能欣賞去程夜航錯過的河岸風光。巧合的是,又搭上來時的輪船,我向服務生解釋沿岸優美風光令人捨棄巴士。我又在長椅睡了一夜,直到頭上的電視播放祈禱經文的聲響喚醒我,驚覺二名服務生伏在跪拜毯上,對著電視機禱告,我急忙起身致歉,內心滿是尷尬,卻忍不住偷瞟他們的禮儀,儘管對伊斯蘭文化充滿好奇,旅人本當入境隨俗,嚴守禮節規範,深恐任何擠眉弄眼的表情,被誤解為輕蔑或褻瀆神明。
過了堅德布爾(Chandpur)恆河與梅克納河(Meghna River)匯合,輪船逆流而上,速度悠緩。午後烈陽照射甲板上,沿岸風光,有如慢速流轉的風景鏡頭。左岸是漫無邊際的黃麻田,右岸是椰樹成林的漁村風光。漁夫頂著艷陽修補漁網;婦人在河邊搗衣;二名孩童揮手吶喊奔跑過木橋;迎親小船敲鑼打鼓與河上船隻分享喜悅;滿載椰子的小船在布袋蓮葉群穿梭…。
我和一名七旬老者就著甲板一方涼蔭並肩而坐,老人四十二歲開始旅行,深覺歲月荏苒,要真誠享受人生不要傷害他人,並強調自己不信任何宗教、不信輪迴來世,認為伊斯蘭教與印度教過度左右信眾的思想,我不點頭也不搖頭,只是微微地笑,我們合照握手留念,卻不知彼此來自哪個國家。
恆河下游流入孟加拉之後,被當地人稱為帕多瑪河,雖然國際上仍慣稱恆河下游,因為宗教信仰的變異,這條泱泱大河不再是聖潔之河,卻是當地民眾千百年來的生活母河,穆斯林不須在河上祈禱、祭神、焚屍,他們日夜仰賴大河航行、沐浴、洗衣、吃喝拉撒,這條生命之河也帶來洪災水漶,滔滔洪水甚至將溺斃死屍沖到數百里外的孟加拉灣出海口,許多低地和河岸家庭隨季節搬遷,過著隨河而居的漁牧生活。
我望著這條陽光流瀉的金色大河,少了悠遠神聖的宗教色彩點綴,只見人類為了生存,與河流相依的真實樣貌。比起在印度恆河畔聖城瓦拉納西繁複的宗教文化與觀光產業交織的雜亂氛圍,遠離達卡的孟加拉的行旅,雖無豐盈的文化、華麗的古蹟建築,卻照見恬淡真切的庶民生活。
孟加拉穆斯林不信來世可能投胎成牛羊或富人,三輪車伕、船伕、搬運工、售報員、煮奶茶或榨甘蔗汁的街頭小販,他們積極改變生活現狀,掙一口飯,比活命還重要,一如該國教授尤努斯(Muhammad Yunus)提倡窮人銀行的堅毅信念,我打從心底佩服孟加拉的阿拉子民。
在達卡的布里甘加河(Buriganga River)碼頭沿岸盡是鐵皮與茅草搭建的房舍,此處堪稱世界最窮的貧民窟之一,男女老少在煙塵瀰漫的環境中出賣勞力,男孩跟隨父兄打鐵、搬磚、載貨,女孩伴著母姊撿拾回收物,似乎在平靜無憂的日子活著,有如黃麻植株不必倚靠任何工具即可抽長挺立。我沿著河畔漫步二小時,慶幸且訝異未遇見任何手心向上的乞者。
我在達卡的唱片行找到羅尼哼唱的歌謠,那是孟加拉國歌《金色的孟加拉,我愛你》,重複聽著輕快悠長的旋律,雖不知歌詞意境,卻想起羅尼踩三輪車的雙腿,望見駱駝背上的男孩,在沙道上奔跑,歷經多年的挨餓與艱苦的磨難,重回母親懷抱,當年駕馭繩索的雙手緊握車把,朝著人生道途前行。
在亞美尼亞教堂,一名日本背包客認為孟加拉若不解決赤貧、人口與水患問題,永遠無法發展成先進國家,並強調這裡沒有印度的豐富文明與古蹟,不會再到孟加拉旅行。
離開達卡的前夕,我身陷布里甘加河船陣,望著金色夕陽流瀉污濁大河,旅程歷歷浮出水面,銘記於心的不是方形、球形、圓筒形的美麗清真寺,而是漂流河道二天二夜的沿岸風景與農家生活。
或許這趟旅程,我不敢正視孟加拉的乞者與不堪的一面,選擇將時間耗在船上,隔岸觀看眾生,仿如旅人保持著嚴謹的分寸,在安全界線裡,才能撫平身處異地的不安。生怕這個貧窮國度的乞者與邊緣人,摧毀遊興。不爭的事實是,我在此住進最破爛的旅館,體驗最簡樸的生活,遇到最坎坷的小孩。
許多從不到落後國家的朋友,得知我到孟加拉旅遊,先是錯愕,接著誇我好勇敢。此時,我徹底明瞭,自己其實是個膽怯懦弱的旅者。
小船泊在岸邊,等待輪船先行,堤岸上脆亮的打鐵聲吸引我的目光,悠晃的光影中,一名獨臂少年,單手握緊鐵條一端,另一端的工人使勁將鐵鎚向下敲擊,少年數度鬆開手,上下甩晃,狀極痛楚。
少年甩動的手,仿若隔空賞我一巴掌,我忽覺鼻酸,忍住淚水,任由暮色圍攏過來,聽著輪船發出噗噗聲響,默默凝視黑暗從貧民窟殘破的房舍中緩緩溢出。
航行孟加拉主要河道的客貨輪船,僅有六間雙人艙房,雨季之外的季節,一床難求。艙房的有錢人,手持攝影機紀錄沿岸河景,多數當地乘客伴著雞鴨、米糧、家電用品橫臥在貨艙地上。為了禮遇外國人,船長讓我在艙房的長椅睡一晚,隔天中午過了大城巴里薩爾(Barisal)才有床位可休息。
船開抵庫爾納(Khulna)已是深夜十點,這艘大船由孟加拉首都達卡沿著恆河下游錯綜複雜的帕多瑪河(Padma River)南下,在河流與小島之間穿梭,漂流大河三十小時,誤點五小時後,鳴著刺耳嘶聲,緩緩停靠終點碼頭。
除了我,來自英國的大學生馬克是船上唯一外國人,我們相約同行,一起找住宿,揹著大背包隨人群上岸,穿過夾道等候親友的群眾,搭上三輪車,前往旅遊書介紹的廉價旅館。
市街一片靜寂,僅有少數小攤亮著燈泡,柔黃光暈投射髒亂路面、破陋屋舍,三輪車伕仰躺狹窄座椅安睡,這座孟加拉第三大城靜如鄉野,即便在深夜,也令旅人感到心安舒坦。
車伕擅自拉車到別家旅館,央求我們更改住宿地點,馬克大動肝火,辱罵車伕,猛踹車輪。車伕才駛到指定的旅館,收車資時,聳聳肩,一臉無辜。我和馬克住進五樓二間相鄰的單人房,每晚只需二百塔卡(約台幣一百元),我假裝沒看見房內蒙了灰塵的桌椅被單,但蚊子嗡嗡繞旋,即使夥計掛妥蚊帳、燃點蚊香,蚊子仍循蚊帳破洞在我腳指狠狠叮咬,我在風扇嘎嘎聲與馬克拍打蚊子的咒罵聲中,沉沉睡去。
清早,清真寺宣禮塔優緩莊嚴的晨禮召喚聲歇止,我到頂樓陽台鳥瞰晨光市景。薄霧散去,灰紅相間的水泥與磚材建築雜亂交錯,對面頂樓打赤膊圍著兜裙的男子如廁後,提水桶沖馬桶,刷牙漱洗,一會兒,出現在一樓街邊向我微笑揮手。街頭人潮漸現,婦女劈柴打掃,烏鴉飛聚塔樓,紡織廠機器轟鳴作響,閃亮晨曦中,庶民真切的生活,皆顯溫暖美好。
我先到旅行社報名隔日前往紅樹林三角洲孫德爾本斯(Sundarbans)的行程,接著搭船轉車,前往三十公里外的巴凱爾哈德清真寺古城(Historic Mosque City of Bagerhat)。當我下公車,一名瘦小男孩牽著三輪車對我招手微笑,另名成人車伕旋即以車頭撞開男孩的車,模樣凶狠,令我打消搭三輪車參訪七個清真寺的念頭。
比起達卡漫天開價、油腔滑調的三輪車伕,庫爾納的車伕多數是文盲,也不欺生,車伕逐漸聚攏,個個連英語數字都說不清,見我堅持不搭車,失望而散。
唯獨男孩踩著三輪車沿路尾隨,他的雙腿剛好鉤到踏板,痀褸的身形,難以跟車伕聯結,我從未見過童工車伕,不禁動了惻隱與好奇心。男孩強調他十三歲,雙腳有力,能操簡單英語和阿拉伯語,當我止步,就拉著我的衣角,哀求我上車。
男孩戴著穆斯林白帽,手腳傷疤累累,膚色黧黑,我們佇在烈日下比手畫腳,當他聽不懂時,只好吐舌微笑。男孩的笑,卸下我的心防,我沒問車資就上車。男孩以跳踩的方式,奮力踏車,屁股遠離椅墊,趿著大拖鞋的腳板,一如小孩開大車,極不協調。被一名只有我一半體重的孩童載著,坐立難安也難堪,仿若所有路人以指責的眼光盯我,二百公尺的距離,有如二公里一樣長。
巴凱爾哈德清真寺古城,是庫爾納唯一可看的景點,雖名列世界文化遺產之林,卻鮮少外國觀光客造訪,即使在著名的薩特庫巴清真寺(Shait Gumbad Mosque)也無提供導覽解說,我只能參考書上簡介,領略寺內七十七個圓形拱頂之美。
男孩在禮拜堂虔誠膜拜,表情肅穆,他的白帽繡著駱駝,三輪車貼有駱駝、月亮、圓頂清真寺貼紙,禮拜跪毯掛於車桿,虔心順服伊斯蘭教教義與真主阿拉。原本哼著歌謠的展覽館的女收票員,竟以阿拉伯語Shukran問候男孩,並敘述男孩曾遭人口販子拐騙到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擔任賽駱駝騎士的悲慘遭遇。
男孩名叫羅尼(Rone)七歲那年,為助家計,遭人口販子以介紹到城市工廠當童工為由,淪落異鄉五年,負責照顧與駕馭比賽的駱駝,十一歲身軀漸長,加上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斡旋,才隨數十名孩童被遣返孟加拉。回到家鄉,人事已非,無法融入原生社會,成為邊緣人。
羅尼脫下白繡帽,翻開帽子內裏印有阿拉伯文及英文標籤,證明這是杜拜某賽駱駝俱樂部的帽子。我看著羅尼鎮定的表情,懷疑這是博取同情的謊言,期待能獲得更多的車資與導覽費。
我在清真寺花園廣場遇到一群中學生與當地旅遊團,他們衣著光鮮,團團圍住我,熱情與我攀談,以照相手機猛拍,我甚至抱著嬰孩與數十人合影。在此享受偶像明星才有的尊榮,合照、微笑、握手,費了一小時才脫身。
我對孟加人圍觀的動作頗感厭煩,我早明白旅行僅是觀看與被觀看,可是一句簡單的「抱歉、不」卻說不出口,頓覺自己是當地居民,他們才是觀光客,而羅尼始終在旁咧嘴笑著。
我和羅尼協議互換角色,由我駕車載他到下一處寺群,這才體會踩車的艱辛,當我搖晃著車頭,小腿使勁踩踏,羅尼坐在後座開懷哼歌,一台路過的公車車窗探出許多頭,有人鼓掌加油,我揮動帽子回應他們的熱情。
遊畢七個寺群,我們坐在湖畔歇息,西斜的陽光投射藍色水面,小而美的清真寺面湖而踞,圓頂倒影映在浩如瀚海的湖面,微風輕揚,芭蕉葉沙沙作響,婦女孩童在此沐浴、戲水,浪花四濺、笑聲滿盈,小雞咯咯叫。
在這安詳舒緩的風景裡,羅尼談起中東生活的甘苦。每次照料的駱駝出賽前,會向阿拉許願,祈求贏得好名次,也保佑自己能在黃沙滾滾的畜牲奔跑驚叫聲中,拉緊粗繩,安抵終點。想家時,就哼唱母親教他的孟加拉歌謠。刺眼的陽光映射著羅尼的臉,他哼著輕快歌謠,瞇成一線的雙眼,淚光閃閃。
眼前這名命運多舛的男孩,只想單純賺點錢或結識朋友,期待早日開一家販售穆斯林宗教文物的小舖。我對於自己先前的猜忌感到愧疚,畢竟累積多年的旅行經驗提醒自己,詐騙的伎倆,日漸翻新,越貧窮的國度,越會利用人性的弱點,交織出看似完美的騙術。有了與達卡三輪車伕,討價還價的痛苦經驗,在背包客罕至的孟加拉鄉村,我只能提醒自己理性小心,別再誤觸人性陷阱。
羅尼的家位於公車站牌旁,是一間以鐵皮、草棚、大芭蕉葉拼湊而成的低矮平房,屋後是大片翠綠金黃的黃麻田,他的母親在路旁擺設茶水攤,販售奶茶與檳榔,獨立撫養五名子女。羅尼的母親急忙拿溼毛巾幫他擦汗,羅尼露出靦腆且幸福的笑容。我坐在攤前悠閒喫奶茶等公車,靜觀這家人的日常生活,羅尼母子目送我上車,一句「願阿拉保佑你!」溫暖我心,萍水相逢的熱情,僅能以多一倍的車資,表達內心的感激。
在紅樹林三角洲沒水電的小島,婦女結伴捧著水罐打水,農民餵雞鋤田、劈柴生火。每日晨昏漫步鄉間小路,隨羊群的步伐前進,熱情的居民不斷邀我入內參觀,他們樂天知命,不乞求金錢、文具、零食。日落後小島漆黑靜默,漫天飛舞的螢火蟲停棲髮梢,蛙鳴相伴入眠,小島的生活讓人感受到與萬物共處的和諧。 我為了一窺世界最大紅樹林的神秘樣貌,搭了半天馬達駁船到三角洲,卻未見孟加拉虎、印度巨蟒、鹹水鱷魚等珍稀動物。還飽受蚊蟲叮咬,過著點油燈、以河水沐浴的原始生活。隨行的船伕說,我是三個月內唯一的觀光客,他每月收入才五十美元,不懂觀光客為何花大筆金錢到此旅遊,達卡動物園就有許多孟加拉虎可看。
回到庫爾納後,我決定再搭一趟輪船,才能欣賞去程夜航錯過的河岸風光。巧合的是,又搭上來時的輪船,我向服務生解釋沿岸優美風光令人捨棄巴士。我又在長椅睡了一夜,直到頭上的電視播放祈禱經文的聲響喚醒我,驚覺二名服務生伏在跪拜毯上,對著電視機禱告,我急忙起身致歉,內心滿是尷尬,卻忍不住偷瞟他們的禮儀,儘管對伊斯蘭文化充滿好奇,旅人本當入境隨俗,嚴守禮節規範,深恐任何擠眉弄眼的表情,被誤解為輕蔑或褻瀆神明。
過了堅德布爾(Chandpur)恆河與梅克納河(Meghna River)匯合,輪船逆流而上,速度悠緩。午後烈陽照射甲板上,沿岸風光,有如慢速流轉的風景鏡頭。左岸是漫無邊際的黃麻田,右岸是椰樹成林的漁村風光。漁夫頂著艷陽修補漁網;婦人在河邊搗衣;二名孩童揮手吶喊奔跑過木橋;迎親小船敲鑼打鼓與河上船隻分享喜悅;滿載椰子的小船在布袋蓮葉群穿梭…。
我和一名七旬老者就著甲板一方涼蔭並肩而坐,老人四十二歲開始旅行,深覺歲月荏苒,要真誠享受人生不要傷害他人,並強調自己不信任何宗教、不信輪迴來世,認為伊斯蘭教與印度教過度左右信眾的思想,我不點頭也不搖頭,只是微微地笑,我們合照握手留念,卻不知彼此來自哪個國家。
恆河下游流入孟加拉之後,被當地人稱為帕多瑪河,雖然國際上仍慣稱恆河下游,因為宗教信仰的變異,這條泱泱大河不再是聖潔之河,卻是當地民眾千百年來的生活母河,穆斯林不須在河上祈禱、祭神、焚屍,他們日夜仰賴大河航行、沐浴、洗衣、吃喝拉撒,這條生命之河也帶來洪災水漶,滔滔洪水甚至將溺斃死屍沖到數百里外的孟加拉灣出海口,許多低地和河岸家庭隨季節搬遷,過著隨河而居的漁牧生活。
我望著這條陽光流瀉的金色大河,少了悠遠神聖的宗教色彩點綴,只見人類為了生存,與河流相依的真實樣貌。比起在印度恆河畔聖城瓦拉納西繁複的宗教文化與觀光產業交織的雜亂氛圍,遠離達卡的孟加拉的行旅,雖無豐盈的文化、華麗的古蹟建築,卻照見恬淡真切的庶民生活。
孟加拉穆斯林不信來世可能投胎成牛羊或富人,三輪車伕、船伕、搬運工、售報員、煮奶茶或榨甘蔗汁的街頭小販,他們積極改變生活現狀,掙一口飯,比活命還重要,一如該國教授尤努斯(Muhammad Yunus)提倡窮人銀行的堅毅信念,我打從心底佩服孟加拉的阿拉子民。
在達卡的布里甘加河(Buriganga River)碼頭沿岸盡是鐵皮與茅草搭建的房舍,此處堪稱世界最窮的貧民窟之一,男女老少在煙塵瀰漫的環境中出賣勞力,男孩跟隨父兄打鐵、搬磚、載貨,女孩伴著母姊撿拾回收物,似乎在平靜無憂的日子活著,有如黃麻植株不必倚靠任何工具即可抽長挺立。我沿著河畔漫步二小時,慶幸且訝異未遇見任何手心向上的乞者。
我在達卡的唱片行找到羅尼哼唱的歌謠,那是孟加拉國歌《金色的孟加拉,我愛你》,重複聽著輕快悠長的旋律,雖不知歌詞意境,卻想起羅尼踩三輪車的雙腿,望見駱駝背上的男孩,在沙道上奔跑,歷經多年的挨餓與艱苦的磨難,重回母親懷抱,當年駕馭繩索的雙手緊握車把,朝著人生道途前行。
在亞美尼亞教堂,一名日本背包客認為孟加拉若不解決赤貧、人口與水患問題,永遠無法發展成先進國家,並強調這裡沒有印度的豐富文明與古蹟,不會再到孟加拉旅行。
離開達卡的前夕,我身陷布里甘加河船陣,望著金色夕陽流瀉污濁大河,旅程歷歷浮出水面,銘記於心的不是方形、球形、圓筒形的美麗清真寺,而是漂流河道二天二夜的沿岸風景與農家生活。
或許這趟旅程,我不敢正視孟加拉的乞者與不堪的一面,選擇將時間耗在船上,隔岸觀看眾生,仿如旅人保持著嚴謹的分寸,在安全界線裡,才能撫平身處異地的不安。生怕這個貧窮國度的乞者與邊緣人,摧毀遊興。不爭的事實是,我在此住進最破爛的旅館,體驗最簡樸的生活,遇到最坎坷的小孩。
許多從不到落後國家的朋友,得知我到孟加拉旅遊,先是錯愕,接著誇我好勇敢。此時,我徹底明瞭,自己其實是個膽怯懦弱的旅者。
小船泊在岸邊,等待輪船先行,堤岸上脆亮的打鐵聲吸引我的目光,悠晃的光影中,一名獨臂少年,單手握緊鐵條一端,另一端的工人使勁將鐵鎚向下敲擊,少年數度鬆開手,上下甩晃,狀極痛楚。
少年甩動的手,仿若隔空賞我一巴掌,我忽覺鼻酸,忍住淚水,任由暮色圍攏過來,聽著輪船發出噗噗聲響,默默凝視黑暗從貧民窟殘破的房舍中緩緩溢出。